出版日期
所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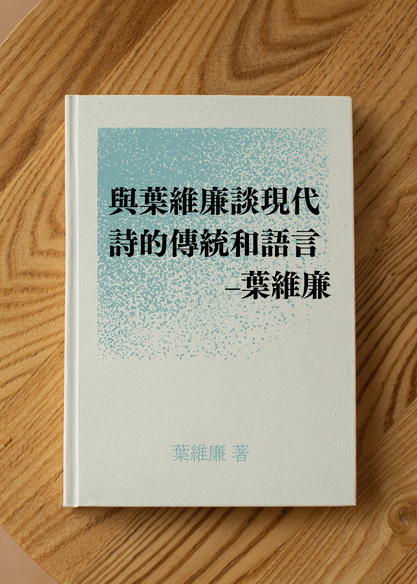
與葉維廉談現代詩的傳統和語言–葉維廉訪問記
- 作者/ 葉維廉
- 發表/
- 發表日期/
訪問:梁新怡、覃權、小克
現代詩與傳統
梁:有人說現代詩脫離了新詩的傳統,但你在過去一篇名為「現階段的現代詩」的文章裏說現代詩甚至是繼承卞之琳、戴望舒他們。到底你和你所認識的詩人們,有沒有受到三、四十年代的詩的影響?
葉:事實上是有影響的。何其芳對瘂弦的詩的意象和句法有影響。洛夫早期的詩吸收了艾青──當然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那種敍述性的句法;卞之琳後期的詩、還有辛笛在意象上的處理,都對我有一點啟發。
談到新詩,問題還可以推前一點來說。譬如說,在一九一六──一七年左右,中國的新學人猛烈攻擊中國傳統的文字,認為舊文字無法傳播新思想,間接做成中國的落後云。但差不多在同時,西方的龐德卻在文章裏稱讚傳統中文的優美,稱之為最適合詩的表達的文字。為什麼龐德覺得傳統的文字這麼豐富呢?原因是它可以去掉很多抽象的意念,而具體地將意象呈露出來,但在五四的初期,完全沒有從這觀點來看待語言,只是覺得當時中國從語言到整個社會結構都是陳腐的,所以要接受西方,一點也沒有考慮到傳統語言表達的好處。
在中國的舊詩裏,詩人往往不會把自己硬加在自然界上面。在舊詩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事件在我們的面前演出,例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就是一個景在演出。事實上,由於我們語言的特色,中國傳統的表達,可以做到不是以個人追尋非自我的意義,換言之,我們不是以現有的組織和規格去瞭解自然界和一切現象,如里士多德用一種邏輯性的骨格來劃分這個世界那樣。
西洋的現代詩打破他們的傳統,吸收中國古詩表達方法的優點。但早期的白語詩卻接受了西洋的語言,文字中增加了敍述性和分析性的成份,這條路線發展下來,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時候,變得越加散文化了。不過當時還有另外一條路線的發展,那就是新月派的路線。新月派在當時相當西化。在這兩條同是接受西方的路線中,新月派開始比較注重「詩味」的問題,雖然是用西洋的形式,但希望不完全是敍述,而能達到自我對物象的感受。
這推進到語言的精鍊的問題,逐漸一直引發到現代派來。卞之琳被認為是新月派的延續,就是為卞之琳他們的語言方面能做到精鍊,不是一種散文的敍述,而是希望够呈露當下的感受。在何其芳的「夜」、「柏林」等等裏面是做到的。尤其卞之琳的「距離的組織」,不是直線的發展而是跳躍過去的:
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
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
報紙落。地圖開,因想起遠人的囑咐。
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兒了?我又不會向燈下驗一把土。
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啊!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其中亦有傳統的句法,如「醒來天欲暮」。在這幾個人的詩中,有很多意象都非常視覺化。
我們經常說詩中的詩味的問題。究竟詩人在選擇意象的時候是在何種心理狀態之下呢?通常我們都會看到很多樹木,但為什麼它不可以成為詩?就是說注意的時刻應當和平的觀看不一樣,你是特別集中注意,脫離了平常的意識狀態。所以「特別注意」,比方說那事物在特別的光的形態之下出現;或者是空間的關係,可能這棟樹在這個空裏顯得很突出,而你注意它那個時刻和你平常時的心理狀態略為不同,換言之,它撤離了一般的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通常我們的時間觀念是很機械化的,一定要離開一點,才會感覺到那個時刻的特別,上面卞之琳、何其芳、馮至等人的詩都是稍微離開平常狀態之下的。比較極端的,就是到達了夢的境界,我們稱之為出神的狀態。玄思的狀態到出神的狀態再到夢都是很接近,要在這等心理狀態之下,那件事物方才會顯得突出,你才可以抓到那件事物特別顯露的狀態。曹葆華有些詩就是這樣的例子。
卞之琳、何其芳、馮至和曹葆華他們一方面受到象徵派和後期象徵派的影響,譬如里爾克,在當時已是那麼流行,他的詩每一首都幾乎是在進入了出神的狀態之下來觀察事物的純粹結晶。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在我國傳統方面同樣也有這種出神狀態之下的詩作,譬如李賀的詩。李商隱的一些詩亦有這樣的狀態。
梁:卞之琳、曹葆華他們並不是很自覺地接受傳統的影響的吧?
葉:我不相信是自覺的。譬如在我自己來說,一直有接觸傳統的東西,而有時在西洋詩裏面,我覺得之中有一些地方是剛剛相交的時候,我自然亦會接受它的做法。這是一種無形中的匯合。我相信在他們這幾個人中,也有同樣的情形產生,但是不是有意就不敢說了。
對於意象的接受和呈露方面,有很多地方我和他們倒有點接近。我覺得自己的詩是略為離開日常生活的觀看方法,而是在出神狀態下寫成的。同時,在傳統的詩裏,如王維的:
人閒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澗中
在這首詩裏面的意方面,本身就是一種出神的狀態,是在一種特別安靜狀態之下看到的事物。
當瘂弦第一之見我的時候,他第一句就說:「我們一定要把敍述性撤除。」這個問題在西洋詩裏面當然很早就提了出來,不過瘂弦和我當時都瞭解西洋的發展,但冥冥中我在接觸詩的時候,我覺得詩應該這樣做,也覺得傳統的需要。所以我是這樣做,他是這樣做,而他坐下來第一句就說如何撤除敍述性的問題,或是用敍述而不會走向三、四十年代大部分詩人那種散文化的路向。敍述性還是可以做的,但在每一句裏面必須要有你個人的聲音和個人的姿態。而不是寫作劃一的口號詩。
幾個階段的詩
梁:你早期的詩和近期的詩有很大的不同,你可以談談這種差異嗎?
葉:很多人都認為我早期的詩比較西化。這句話一半是真的。因為傳統的詩短和比較簡單,而我的詩比較複雜,我既是承繼新詩的傳統下來,我仍然採用敍述性,但我敍述的形態跟他們不同,如用很複雜和多層次的表達,如果說這不是跟西洋的表達方法有一點互通聲氣,那是騙人的,到底傳統的詩並不是這麼複雜呵。事實上,當時我想嘗試能不能將西洋和傳的表達手法構成一種新的調和。以「賦格」為例,個別意象的構成和傳統的關係很密切,但整體交響樂式的表達卻接近西洋的表達方法。
在最早的時候,究竟西洋傳統重要抑或中國傳統重要,完全不是我們考慮的問題,我覺得,我作為當時一個現代的中國人,作為一個被時代放逐的人,出國之後空間的距離使我更有被放逐的感覺,我的感受複雜而且有一種游離的狀態,在當時來說,我只是忠於我自己的感受。由於我對兩個傳統多少都有一點認識,就產生了那樣的詩。沒有考慮到究竟應否這樣,只覺得我忠於自己就好了。但是我又覺得,自從我繼續寫下來以後,對中國傳統更加進入以,尤其當討論更多中國傳統的詩的時候,我相信中國傳統是比西洋傳統更適合我,所以我有個趨向是漸漸回到更多的中國傳統。
我在鄉間長大,對山水有很大的愛好,在我詩的裏面有很多山水的意象等等,但由於我面對的是很複雜的情景,是東西方的揉合,有兩方面的衝突。而我最近的詩,仍有這種情形,但中國的成份比較重,趨向喜歡用短的句,簡單的意象,希望用簡單的意象能够達到複雜的感受,而不是用以前那末繁複的處理方法,你知道,這可能是跟我胃病開刀也有點關係啦……。這也是一個可能,因為找鬱結得太久了,所以我寫完「愁渡」之後已經開始放鬆自己,我不希望再陷在這種深沉的憂時憂國的愁結裏面,所以我自己衝出來,特別選擇其他的題材來寫。當然啦,你看我在「醒之邊緣」裏面是否完全已經脫離呢?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很多主題和感受都重新出現,只是比較放鬆一點。剛才說與我自己開刀有關係,因為我的胃病可能是這種鬱結的一部份,現在要自己盡可能清心寡慾,或許這樣會影響我現在的詩也不出奇了,但不一定是這個理由。
梁:「愁渡」寫了多久?
葉:兩個星期左右,是斷斷續續寫成的。
梁:你那首詩寫得最久?
葉:寫得最長時間的是「降臨」,最初先寫了兩段,在「筆匯」發表,然後就等了很久才寫第三段,之後就寫得快一點,第四段是在香港寫的,所以其中有一些香港的意象,比方把城市看成碑石的那種感覺……。
實際上,一首詩的產生……起碼這一點我們是與三、四十年代的詩人不同的,他們的主題幾乎在腦袋裏構想得非常清楚,知道寫些什麼,寫給怎麼的對象看,然後再在意象上推進一步。對我來說,不是這樣,有時是一個意象將我捉住,使我迷惑,然後由意象而發展成一首。或者有時是一種非常鬱結的感覺和心情引起,開始寫,寫出了一兩個意象之後,再由這些意象引發寫出整首詩來。所以鬱結了一段時間之後,一寫差不多就寫出來了。當然我也有修改。「降臨」的初稿,和後來有分別的,主要是第三首。已經寫好了,我覺得不够力量、不够濃縮──濃縮是當時我嘗試的一個特色──所以後來再改寫。
小克:在「愛與死之歌」的後記裏你說這五首詩來的時候你是毫無防備的,這麼說,你以前的詩不是這樣的了?
葉:在以前,一起來的也有;但來的時候,我──也不是有意這樣做的──不是馬上就寫出來,差不多醞釀一段時間,有時句子在腦袋裏,有時覺得那種感受仍未够濃,到了够濃的時候,一寫,那些意象就一直生長,這樣就一直寫下去了。
梁:「愁渡」是怎樣寫出來的?
葉:這首詩是怎樣寫的嗎?以前我有一首用英文寫的詩裏面有著一種旅程的傾向,我很想將它寫成中文,但寫了很久也不成功,我寫了開頭,開了頭後我覺得不需要寫那首,改寫這一首,寫了第一段,後來第二段第三段就慢慢地成長。這詩和其他詩的組織不一樣,它有很多敍述性的成份,是變遷的,每一個視點都不一樣。第一曲可以說是一種平地上的回憶的觀察;第二曲是在高空上,第三曲是一封信的形式……即是說,同樣的事件用五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是這五個不同的角度怎樣以同樣的風格出現,所以在語言上面就是要有相當的用功,但我覺得自己一做就做到了。「愁渡」五曲的接觸方法都不同,但語言要能够御到有一貫的力量,所以在節奏處理方面比較重視。
在「愁渡」詩裏,用上很多傳統的句法。第四曲這兩句:
千樹萬樹的霜花多好看
千樹萬樹的霜花有誰看
這兩句最重要的聲音是在後面,是杜甫詩的廻響,用來傳遞那種心境。用古詩,不一定是要像艾略特那樣作為典故的引喻。
有一樣事情是我自己沒有想到的,為什麼「愁渡」之後要離開呢?我記得這首詩和「賦格」的結構很接近,不是有意的,寫完了之後才發覺,原來我一直都在這個「結」裏面,沒有走出來,所以我一定要離開這個心態和這個主題。
梁:「愁渡」這名字有沒有這個意思?
葉:「愁渡」這名字是後來才加上去的。這詩在很多地方和「賦格」很接近,特別是結尾的地方。在這以後,我才知道我自己鬱結在這個情緒之中有多久。所以我一定要放棄。這些都是後來才想到的。
梁:「愁渡」可不可以說是有一個故事的?
葉:故事是在後面而不是在前面。我們和三四十年代詩人最大的分別就是在這裏。他們的故事在前面,我的故事在後面。我將故事的好幾個重要點的感受採下來。每一首抒情詩應該怎樣寫的呢?抒情詩一定要將感受的輻度呈露出來,而不是將故事講出來。換言之,譬如聽一首歌,音樂表現出它的肌理,你感情的肌理。在「愁渡」詩裏面,肌理當然有了,故事是在後面而不是在前面,這個故事是可以重串出來的。
詩的語言
梁:在你早期的詩裏,一直有用古典的文字或者借用古詩的文字,這究竟是擺脫不掉的懷戀,還是另有深意?
葉:這裏面是有著兩個情況:一個情況是我覺得在我利用一首舊詩的時候,有很多地方可以將在舊詩裏非常濃縮的氣氛和感受,帶到我詩裏面需要這樣表達的地方;另外是我在那個時候始終覺得白話有很多缺點,這些缺點是文言的濃縮可以補救的。所以我許多把白話和文言儘可能混合到不可以分開。譬如有些朋友覺得我的「游子意」裏面和「愁渡」這階段的混合的嘗試比較成熟。但是我在這之後卻盡可能放棄這種做法。但也不一定能放棄。相信我對舊詩的愛好實在太深,理論上,我並不是沒有想過要不要寫大眾詩這個問題,可能我對傳統的東西有很多非常深厚的感情,這並不是一下子可以擺脫得了。
讀者麼?當然還有讀者的問題。但讀者是指那些人呢?你寫詩的時候,會想到你的詩是寫給誰看的。我寫的不僅是給某一種中國人看,我有一種心靈上的交往,是關於整個中國的傳統問題。我將我的意思傳達給一切中國人,我寫的時候,可能有許多觀眾已經是缺席的了。
我對於中國的關懷,我希望有人和我分擔這個經驗。而且,我很希望通過我的詩的創造,能够使別人進一步對於傳統有所愛好,這個是自然的做法,問題是我們願意不願意完全將傳統放棄,但我本身是不願意的。我覺得在傳統裏面有很多好的東西,希望別人能够進入去得一些東西然後再走出來。這未必完全是有意的,可是在寫詩的時候,這顯然亦是一種次要的考慮。
在我心底裏面有一種很嚴肅、認真的想法,就是擔心我們這麼多年的中國文化的演變裏面,會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我們基本上對藝術的愛好,對於中國傳統的藝術的感受,可能會慢慢淡泊到消失。
梁: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希望憑藉你的現代詩把讀者帶回去傳統?像一座橋那樣溝通現代和傳統?
葉:不一定是帶回去。是有點像橋。希望在讀者的口味方面,能够保持有某一程度的認識或者或感受。這些並不是像教書般的說法,而是希望能通過詩,有一種附和、有一種可能……這只有憑藉詩才能做到。
梁:詩人對文字是有一種責任的。
葉:對。龐德說過:「詩人的責任是淨化該民族的言語。」這方面的好處和缺點都很明顯在我的詩中出現,缺點就是說,可能由於我這樣的做法的時候,我所提煉的詩是藝術的語言,藝術的語言在現代社會裏面應不應該嘗試?站在文化上的立場來說,像是應該這樣做的,不是嗎?但藝術的語言在現代這樣急促、這樣動盪的社會裏面,不能够達到讀者。我們所提煉的語言是應該從很普通的民間的語言裏面提煉,還是應該在文學的語言裏面來提煉?這中間就有了衝突和選擇的問題。我們是應該以現成的、很有成就的藝術的語言來調劑我們民間的語言,抑或以我們民間的語言來做最後的標準?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那麼在傳統裏面不是有兩條線可以走嗎?我可以走樂府的語言(民間的語言)的路,我可以走唐詩的語言(藝術的語言)的路。我們看李白在樂府裏面提煉那麼多的語言和好的句子出來,我相信最後走的路線應該是走李的那條。事實上,我在「賦格」裏面就有一種這樣的做法和想法,即是說,是一種口語化的語態,但卻是比較提煉的語言。 譬如「君不見……」並不是純學古人那麼簡單的,那裏面有一種廻響在。李白這句子從那裏來的呢?是從鮑照來的。鮑吙最早在樂府裏面就有「君不見……」的寫法,問題當然不是在一兩個例子,問題就是到底所謂在民間裏面所提煉的語言,和在傳統裏面吸收滋養來培養民間的語言,這兩者間的調和及選擇。我自己一般的傾向,大概是先在白話和文言之間提煉了一種語言之後,而以這個基礎再來調劑一下民間的語言,如果這麼作,也是我的一個嘗試,但可不是預先有計畫地做的……只是我曾經想到過這樣的問題。
梁:這樣的情形,現代詩人中有沒有做過?
葉:有人做過:方旗這麼做過,雖然還有點問題,但有很成功的口子。其實以前的廢名便已開始這種試驗了。
葉:過去三、四十年代的詩人的詩人中,有好幾首詩的結構和傳統詩很接近,譬如艾青的「北方」,這首詩如果和李白古風比,它雖是用白話來寫,在意象上卻很接近。……徐志摩有一首詩寫在晚上聽到琵琶的聲音,就跟李白有一首詩在表達的過程上非常相近,當然他受到西洋的影響,兩詩的組織已不相同了。梁文星亦有一首「彈琵琶的婦人」,以白話來寫白居易的「琵琶行」。我的詩裏也有一些這樣的例子,不過,我不想在這裏說明太多,那沒什麼味道了。我相信,傳統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創作與理論
梁:你現在除了寫詩還教書,作一個學者和作一個詩人,有沒有衝突?
葉:有,當然有啦。你知道研究學問是知性的、分析性重的工作,而且也有點兒死功夫在內……。寫詩可不是這樣,寫詩的過程不是這麼邏輯性的,所以這可以說是兩個世界,有時是可以分開來的,彼此剛好是走極端的情況也有。這兩者之間究竟有沒有相互的影響,我看得由別人來判斷了,我自己對這方面並不特別注意,但我寫詩時,有時完全希望跟我做學問功夫的那種思維過程互相隔絕的。但在我的理論所提的東西,譬如對於傳統的了解,對我的詩有沒有影響,這裏就很微妙了,有時有,有時沒有,有時是一種挑戰。我明明曉得,比方說,在敍述性的寫法裏不可以做到某種境界,因為敍述的時候,自然就會參與了人的意思了,參與作者的意見了。但是有時又會嘗試,能否在利用敍述的時候達到另一種境界,這是一種挑戰。
……談了半天,其實是這樣的:寫詩呢,最初並沒有這般的嚴肅,寫詩實則上是過癮,寫下去,自己覺得心裏有種鬱結給寫了出來,有時自己很驚異,可以有這麼的意象在你手中出來,很是愉快,因為創造了一種境界。最早是這麼的寫,當然寫的時候,語言的問題自然就會嚴肅了,會想怎麼才做到合自己的意思為止,當然每個詩人都應該這樣做的。到了後來,慢慢地成形,或者成為一種風格,成為一種我的聲音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在自己的風格裏面發展的階段。那麼,至於說:「現在葉維廉是不是有一套理論呀?」這是後來逼出來的,我寫的理論並不是針對自己的詩,而是針對其他的東西而寫,事實上我很少寫及詩的理論,我避免寫詩的理論,有幾個因素:第一我寫詩的理論,是不是要替自己的詩辯護,是不是要替自己的詩構成一種理論呢?第二,我寫詩論,該舉什麼例呢?當然我不希望舉自己的詩為例,但如果舉同行的例,就會有人說:你說他的詩好啦我的不好啦,好像重彼輕此似的。我早期談詩的時候,多舉西洋的為例,並不是說我的意見不適合中國的現代詩,只是怕引起誤會罷了,所以我往往多寫其他方面的詩論。
而現在有些人卻以我談詩的文章來看我的詩了,這有時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比方我在談王維時談到「純粹經驗」,有人就以為這是我對文學的全部主張。其實只要他們仔細看我的論文集「秩序的生長」,就會發覺裏面而接觸的幅度其實要濶一點,並不光是談那麼幾個問題。
梁:而且你也提過:理論和創作一樣,應該不斷發現新的可能性。說到其他方面的批評,你寫過一冊討論現代中國小說的「經象、經驗、表現」(即「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你當時談小說比較喜歡偏重技巧方面的討論,現在你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葉:本來討論小說也好,詩也好,這兩方面的內容和形式是分不開的,不過在討論的過程中,通過表達的形式來看內容,還是通過內容看形式,這兩個偏重寫起上來是有點距離的。當時我討論小說的時候,覺得一般人對於小說作為一種藝術的觀念太稀薄,那麼的隨便寫寫就算了。譬如說你要寫個小說嗎?當然是有個人啦,他在某個地方出現,由於他在那一個地方出現,就先描寫那個地方了,之後呢,就是對白了,一定是平鋪直敍的發展下來。但是,究竟寫一個場境的時候,有什麼藝術的作用在裏面,往往卻沒有去考慮。又究竟可不可以做成一種氣氛?這種氣氛對以後的發展是不是一種應合的作用,許多小說都沒有考慮的。我寫那些文章時,有一部份原因是希望在那方面的問題,並且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等等。但是,以後如果再寫這方面的文字,我希望在主題和技巧兩方面都兼重。但當然,我仍堅持小說不是隨便可以亂寫的。
兒童詩及其他
梁:你有沒有寫過討論其他藝術的文章,比方說論畫的,你寫過莊語……
葉:還有沒有寫過其他論畫的?我談過不少,但沒有怎樣寫過。不過我大概會寫一篇談談中國現代畫的傳統,這跟我們實際上是很接近的。
覃:你自己也畫畫吧?
小克:「界」那首詩就有詩也有畫……
覃:那畫古怪怪,文字似的。
葉:鬧著玩吧了,這些甚至也不可以說是副業。
事實上是這樣的:我對畫很有興趣,也有相當感受,我也藏有一些現代人的畫,多是別人送的,我沒有錢,不然可以買一點。對於畫,尤其對於西洋畫來說,後期印象派一直下來,它們和我們的整個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因為喜歡畫,所以自己有時玩玩,畫一兩幅;通常並沒有畫什麼大畫,有時聖誕節,弄一張小小的,寄給朋友,我自己沒有存的,寄出去,玩玩吧了。「界」那幾張是玩出來的,先畫了,才寫詩。我並不是畫家。但有好幾次也想過放棄詩去畫畫。為什麼呢?最大的問題就是,我覺得語言裏有很多拖泥帶水的東西,畫比較直接,在表達上,有時就那麼畫下去,很痛快。如果我並不是存心要做一個職業畫家,這是沒相干的,我畫給自己看罷了。其實寫詩也可以是這種態度,我最近就有這樣的態度了,即是說,並不是一定要寫到怎樣嚴肅的程度,我寫得好就好,不好的話,我放在一邊吧了。這樣,人可以開心一點。我覺得我的詩太憂鬱,太多憂結了。我現在想寫點「快樂的詩」。當然,這種快樂詩和「光明」詩是不相同的。(眾笑)
小克:你寫給兒女的詩呢?
葉:(笑)我很希望寫一組兒童詩,也寫過一點。我覺得我們的兒童的文學傳統太瘦弱了。外國人有一本一本給兒童看的詩,就算是文字遊戲也好,但是寫得讓小孩子看來都很愉快。我們的兒歌呢,是以現有的節奏性加上文字的,逼他們讀什麼五個字七個字「天上一顆星,地下一塊冰……」這些,我認為不很够味道。我很希望寫一組比較自由點,有些韻的……
梁:配歌的?
葉:我有寫過配歌的詩,我寫過一二首Hit-song和rock music的詩。我有一首李泰祥已經譜好了,是用吉他彈的。另外還有一首,本來打算灌唱片,後來因為幾種因素所以又擱置了。還有一首「生命之歌」,寫得比較早,是別人叫我寫的,已經可以唱的了(葉維廉隨口用國語哼了幾句),但並沒有唱片,只有一些錄音。這倒不是什麼rock music。我在多方面都有點興趣,但始終沒有做下去。我最可能會做的,還是剛才說的有關兒童的詩,我覺得兒童實在太可憐,沒什麼可看的,很多兒童刋物所寫的都沒什麼意思,能够寫點兒童詩實在是好的。
覃:好像英國的史提文遜就寫過很多兒童詩。
葉:甚至我可以用外國的兒童詩來作個藍本,這當然不是為了自己,我覺得,如果孩子們可以吸收一些那樣的語言,這應該很有意思。不過我又想,這個工作應該由瘂弦來做,因為他的國語比較單純。
梁:你們可以聯合幾位詩人,每人寫一首。再請畫家們配畫,出一本美麗的書,給小孩子們當禮物。
葉:或許這趙我去臺灣後會這樣做。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小孩子一旦喜歡了詩,感應了那種節奏,以後定會得益不淺。我唯一做過的,是寫過一首「漫漫的童話」,那時想寫兒童詩的,不過越寫越深奧(眾笑),但仍有點兒童詩的意味。兒童詩有一個好處,想像可以自由,像我們看卡通一樣,在卡通裏面,一隻死掉的貓可以再生,打不死、跌不死,有了這樣的自由,寫起上來,可以寫出很精采的意象,而且小孩子們會喜歡,不像什麼「上大人,孔乙己」……要小孩們唸這些,簡直沒有理由的。中國的兒童實在太可憐了,其實想像是可以飛騰一點的。
覃: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後,對兒童的感情才深厚起來的吧?
葉:這個當然是了。我本來就很喜歡小孩子。有了孩子後,當然更深啦。我對外國的兒歌都很熟,以前有個時期每天晚上都讀給孩子們聽,所以有很多我都可以背出來,反而我自己的詩都不能背(眾笑)。我真的不會背自己的詩,說出來也沒人信。
有些朋友不喜歡我現在的詩的轉變,現在我的詩好不好可以不說,但對我自己來說實在是有一點好處。因為我能够脫離了那種那麼濃縮的鬱結的心境之後,就什麼都可以寫,什麼都想寫。但回來香港這幾個星期,一直卻想寫一首很濃縮的詩,寫不寫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想寫,但我又不想回到那麼濃濃的鬱結……。
覃:是那方面使你還寫不出來?
葉:社會。你走出去就是這樣的了,人擠逼,空間也富……。
覃:為什麼過去在香港你可以寫得出來,而現在又不可以呢?是突然又不習慣嗎?
葉:不是不可以寫出來,如果我寫出來,像過去那麼繁雜濃密的詩,我又不大願意再進入那種鬱結的心境,但現在又有這種的衝勁寫這樣的詩,現在真的很想寫一首閞於香港這樣的詩……。
葉維廉
性別:男
籍貫:廣東省中山縣
出生地:
出生日期:1937年
學經歷
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加州大學分校和聖地牙歌加州大學,兩度回國於台灣大學任教。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