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
所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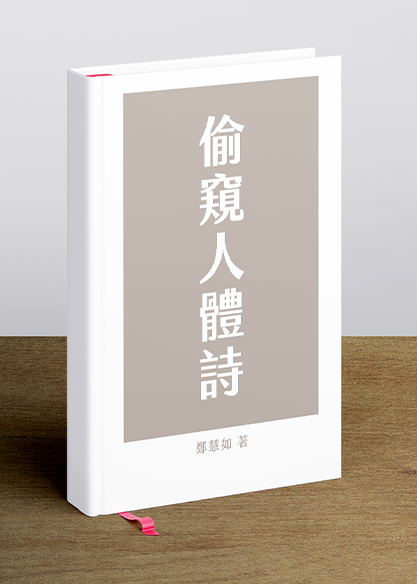
偷窺人體詩
- 作者/ 鄭慧如
- 發表/
- 發表日期/
—鄭慧如 以《新詩三百首》為例
一、從身體到肉體─一個文學史的課題
人體既是知識的對象,又是認識的主體。在生活中,知識的對象與認識的主體相互交纏拉扯,無法截然二分。在經驗上,兩者也常常重疊掩映,指導言行,以便和社會對應。
倉頡造字之初,就已知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說文‧序》),只是彼時人體不過是造字的材料,缺乏主體意識(註)。中國文學正式而較具規模地把人體當成客觀描繪的對象,應該發端於六朝宮體詩。宮體詩裏,凝視人體的層面從身體(body)到肉體(flesh);從粗糙而原始的功能特質,到精緻而綿密的欲望特質(註)。宮體詩以降,「晦淫晦盜」的小說,便每每浮現人體時隱時現的主體意識(註)。自是而後,中國文學中的人體素描,就頂著血肉模糊的天靈蓋,抵禦道德家張牙舞爪的狼牙棒,一路跌跌撞撞,以迄於今。
中國現代文學,撇開其他文體,單就新詩而言,描繪人體的作品可概分為二:一是以身體來冥思,一是以身體來論述(註)。前者的正文(text)傾向溫柔敦厚的美學品味;後者的潛在正文(subtext)(註)則往往遍佈權力的刮痕。
人體究竟是不是詩人最初及最終的信仰呢?是否詩魂幽囚一生,終於失去自我?或是詩人可以超越耳目口腹之欲,超越思慮判別,找到一個明淨的秩序?不管是論述或冥思,詩人的目的在哪裏呢?如果是猥褻,怎敵連綿《一千零一夜》的香豔?如果是自由,怎敵鄭衛的合獨之風(註)?如果是警告,又怎敵《紅樓夢》的太虛幻境?然而世上本來沒有說不完的新鮮事,所謂詩,正是舊材料的新綜合。就冥思人體的作品而言,唯其是舊材料,所以讀者能夠了解;唯其是新綜合,所以和實際人生有距離,可以避開習慣,超越濫調,隔著透視鏡返照人生。就論述人體的作品而言,唯其是舊材料,所以詩人便於翻覆;唯其是新綜合,所以可以棄絕皮肉,訂製身份,打造另一個自己。讀者也是如此:一方面要拿實際經驗來印證作品,一方面要掙脫實際經驗的束縛,打破固定的、被迫接受訊息的位置。
本文即以《新詩三百首》(註)為例,析剔其中的兩種身體素描。
二、人體─作為一種論述
所謂「以人體來論述」,意謂詩人以較具象、結構、多樣、感覺統合的文字表達,顯示權力結構下的「我」。詩人與被體制馴服了的身體對話,呈現真誠的感情世界或童騃式的人生目標。八○年代初期,這類作品尚有極濃厚的實驗意味(註),往往動搖了歷史、文化、心理、習慣、價值觀,帶動一種「狂喜式」(Jouissauce)的閱讀(註),令讀者不安、不舒服、若有所失,進而有窺探的欲望(註)。
引起讀者窺探欲的因素,常是詩人「建構」了一個悲劇─他們睜大眼睛,向平常人所易避免的災禍裏闖,並告訴讀者:冥冥之中有些搗蛋鬼,讓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一般說來,悲劇的主角,或由於其對抗不幸的努力,或由於其陷於宿命的悲愴,遭遇愈苦,愈予人崇高雄渾之感,但是肉體/性的悲劇主角卻是例外。因為性/肉慾,雖不能說是壞事,究竟不易給人崇高的印象。而對於某些人而言,肉慾只是一種慾望,一種逼迫。因為不能節制這種慾望而淪入痛苦或不幸,甚為悽慘可憐,但不崇高;因為追求肉體自主而遭來異樣的眼光,甚為無辜可憫,但不崇高。在生命的意義上不崇高,就敘述這件事的文學境界而言,也不崇高。尤其要是有人陷於泥沼而不能自拔,只求肉慾而無自尊,其罪惡感、無從救贖感,更令人不忍卒睹。顯而例之,好比宋元時代的中國,「難耐空閨寂寞」便是一種笑語,一種令人鄙夷的失德。說「難耐空閨寂寞」的女子「脆弱」,很「恰當」,也很容易。落實到文學作品中,便有未能免俗的作者,先設定一對才子佳人,歌頌其才情美貌一番,以便賦予他們在情節中談情說愛─其實是翻雲覆雨─的權利。作者不痛不癢地掛羊頭賣狗肉,讀者也半推半就地恣意窺伺。例如《西廂記》裏「軟玉溫香抱滿懷,春至人間花弄色,露滴牡丹開。」幾句詩,便是寫男女交歡,只是讀這幾句詩時常常叫人忽略其本意。因為其描寫方式美麗而出微。這種美麗而出微的描寫,不但迎合了「思無邪」的文學觀,躲開道德家的鋒刃,拉攏了較多讀者;而且掌握了現實和文字之間距離─因為在實際生活中談男女間事,話不會說得那麼漂亮。拿這幾句詩和伊蕾〈我的肉體〉(註)比較,分別立見。〈我的肉體〉這樣說:
我是深深的岩洞
渴望你野性之光的照射
我是淺色的雲
鋪滿你僵硬的陸地
雙腿野藤一樣纏繞
乳房百合一樣透明
臉盤兒桂花般清香
頭髮的深色枝條悠然蕩漾
我的眼睛飽含露水
打濕了你的寂寞
大海的激情是有邊沿的
而我沒有邊沿
走遍世界
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純潔的肉體
我的肉體,給你的財富
又讓你揮霍
我的長滿青苔的皮膚足可抵禦風暴
在廢墟中永開不敗
這是「豁出去」的寫法。詩人企圖拋開虛偽與愛情的包裝,直接進入色慾的爽朗。從末句「在廢墟中永開不敗」,可知詩人自許為末世荒原上傲視群倫的鮮花,向「你」敞開自己。換言之,詩人應是試圖透過一副美麗的女體,展現女性之美。然而在花團錦簇的文字裏,讀者感受到的恐怕不是吸血的女性之美,而是供養的母性之美。詩中出現的意象,諸如岩洞、雲、野藤、百合、桂花、枝條、露水、大海、青苔,這些覆育大地的景物,很難不給讀者「大地之母」的聯想。
夏宇〈蕃茄醬〉以「海太深了/海岸也不知道」告訴新婚的朋友:女性的「海洋」太深廣,對於新郎並非福音;而伊蕾〈我的肉體〉卻說「大海的激情是有邊沿的/而我沒有邊沿」,如此追求情慾自主,無寧非常危險,有「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之虞。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詩人擺出神女(女神)的形象,再以文字呈現,不但質疑了藝術所謂的「真實」,也挑戰了一般人印象中的女性氣質。於是,潛在文本遂穿梭遊織於地母變體的勞動婦女形象,及資產階級的都會知識女性之間,以其陰性風格,揭露剝削「我」的男性機制(註)。無奈就文本來看,詩人的身體仍約束在既定的脈絡裏,所以詩人僅能藉著想像,成就「你」(男性)開發「我」(女性)身體的優勢。就〈我的肉體〉而言,作者的主體意識與其說是建立在身體的實體功能上,不如說是建立在流動而無法範圍的慾望之上。尤其如果試著把詩中的「你」改成「我」、「我」改成「你」,更可發現此詩完全擬仿男性語言,並無開放出任何顛覆的空間。(註)
身體和心靈,正如現實世界和文字符號的關係一樣,往往既相依又矛盾。當熱情正熾之時,總想及時行樂,以歡樂衝決一扇扇的生命鐵門。然而所有的快樂都有它的期限,不太經用;所有的快樂也都跟其他的情緒一般,頂點一到達,便只有下坡路可走。五味所以令人口爽,五色所以令人目盲,意思大概也在這裏:人體這個小小的皮囊,所能承受的歡愉極其有限,承受痛苦的幅度反而可能無限。波特萊爾《惡之華》中,把愛情及藝術的對外關係,解釋為賣淫:情人讓對方佔有自己、藝術家讓欣賞者投入自己的創作,皆屬賣淫。他透視地獄之美,但是念念不忘的,其實是人世之美。而那種美,他在罪惡之中,地獄之內,各種匪夷所思的時空裏看到、想到。總之,在他所以為前輩詩人沒有發掘的地方看到、想到。不論是肉體或心靈,「背棄」可能只是一種方法、態度,提醒詩人走在語言前面,避免相同的結構、意思、字眼,擺脫社會的疏離、異化作用。如果詩人關注的焦點常在心靈和肉體之間擺盪,那麼,也許不見得是進退失據(註),而可以解釋為:詩人和關注的對象之間,維持其淡如水的關係,例如有時在文字中縱欲狂歡,有時扮演矜怯的情人。倘若和關注對象過於密切,變成撕不開的朋友,終了怕只剩苦痛和狂喜了。
陳克華完稿於行伍中的〈我撿到一顆頭顱〉(註),跨越生死幽冥,從沿路撿到的手指、乳房、陽具、頭顱、心臟,畸零摧傷乍見。為了營建風格,詩人「外造」了相當勉強的敘事者:「我」,是種造境;然而其纖毫畢現的手法先足懾人。例如這一小段:
之後我撿到一顆頭顱。我與他
久久相覷
終究只是瞳裡空洞的不安,我納罕:
這是我遇見過最精緻的感傷了
看哪,那樣把悲哀驕傲起的唇那樣陳列
著敏銳與漠然的由玻璃鐫雕出來的眼睛那
樣因為痛楚而微微牽動的細緻肌肉那樣因
為過度思索和疑慮而鬆弛的眼袋與額頭那
樣瘦削留不住任何微笑的頰──我吻他
感到他軟薄的頭蓋骨
地殼變動般起了震盪。我說:
「遠方業已消失了嘛?否則
無能將你亟欲飛昇的頭顱強自深深眷戀的
軀幹
連根拔起?」(註)
這段文字銳利如剪。其中詩人體悟唇、眼、肌肉、額頭、眼袋、臉頰的部份,刻意不加標點,造成視覺及呼吸上的困難,結晶為一種堅硬的詩風。如同哪吒剔骨還父,挖肉還母,〈我撿到一顆頭顱〉一詩,代表一場身體與體制斷裂的儀式;還可能更多義,代表「吾之大患,為吾有身」(註),或是宣揚生命在不確定之中那份真實及自由的意志力。在其熱辯與激語中,所有的罪惡(如果有的話),都帶著深深的魅力。例如:
之後我撿到一只乳房。
失去彈性的圓錐
是一具小小的金字塔,那樣寂寞地矗立
在每一個繁星喧嚷
乾燥多風的藍夜,便獨自汩汩流著
一整個虛無流域的乳汁──
我雙手擠壓搓揉逗弄撫觸終於
踩扁她──
在大地如此豐腴厚實的胸膛,我必要留下
我凌虐過的一點證據。
詩人「虛擬實境」,捕捉盛放的生命和赤裸裸的死亡。相對於前引「我撿到一顆頭顱」一段,一邊是逼人的乳房,飽蘸著活力;一邊是血肉全銷的白骨,以空洞的眼眶,看著大千殘破後的身體部立,成為生命的嘲諷,然可憫。藉著身體與文字的對話,詩人訂製一個自己,開展認識自己之途(註):形銷骨毀的「他」和撿拾者「我」,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敘事者陳克華?「失去彈性的圓錐」和「豐腴厚實的胸膛」,究竟哪一個是敘事者的乳房?看起來冷酷腐敗,其實形銷骨毀─然而,在此的「其實」果真比「看起來」實際嗎?勞倫斯的阿拉伯裝扮,模仿阿拉伯人模仿到促使阿拉伯人反過來模仿他(註);麥可傑克森徹底白化,可能比多數白人還要白。強調傑克森和勞倫斯的「本來」身份,未必比較切合「現實」:現實原來就不只一種。
因為詩語重擊歇斯底里的浮華世界,引導讀者進入此詩的潛在文本,思索種種生命中的緊張:例如身體/心理、性別/肉體覺醒、生理性別/文化性別(註),甚至天分才情/時間生命,都存在一種拉鋸的緊張。故而,結尾:
我將他擱進空敞的胸臆
終而仰頸
「至此,生命應該完整了……」當我回顧
圓潤的歡喜也是完滿。
就像章回小說例有的大團圓結局,不但使得還逗留在詩行中的讀者頓失所依,而且似乎或多或少透露詩人妥協的痕跡。
蘇金傘的〈頭髮〉(註)一詩,呈現華洋雜處、新舊掩映的闌珊,可視為一種殖民心理層次的翻轉。父親的長辮子承受了祖父及差人的暴力,拖進棺材仍舊粗大,象徵不畏威權的血液。在詩人身上,這血液突破頭蓋骨,成為鬍鬍的硬髮,「叫人看著不順眼」。首段寫父親的頭髮,殖民/被殖民者的關係營構在父親/祖父及差人之間,形成兩者對立狀態下的相互抗爭、否定與排除。三段寫敘事者(我)的頭髮,殖民/被殖民者的關係,則充滿身體表演和影像操弄:
於是在人面前,
我總是用手按住頭髮,
不讓它崛起,
替我惹禍。
但頭髮太硬
真是無可奈何!
手指一疏忽,
就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
最後我把它剃光。
但又有人說:
這是秘密組織的標記,
應該用刀連根割下來!
敘事者的抗爭方式顯然不似其父。這是一種表面臣服而內心騷動的表演,「頭髮」在此,成功地達成象徵的任務。敘事者(「我」)按住頭髮,一如按住賁湧的血液,以避紛端。他的選擇並非全然自由──自由之中,有一絲不得已。
從某個角度上來看,人體是新興、現代、強橫的政府,所攻佔的最後堡壘。在政治上,政府視人體為國家的財產;在經濟上,資本家視人體為生產的工具。國家可以有權剝奪人民生命、施以苦刑、切除部份肢體、在身體上烙印,發生傳染病,可以隔離個人、房舍、船隻,甚或整個城鎮。有政治運動,可以把異議份子列入黑名單,或放逐,或監禁(註)。軀體,其實一直受到一的監控(註)。人體和政治對決,不止是肉體的抗爭而已,往往牽涉到性格的操練、意志的頂撞、智慧的周旋。那些抵禦霸權的聲音和形象,遂撘建了現代鳳凰的烈火祭台,而他們從劫灰中重生的指望卻是微乎其微。伴隨著鳳凰的劫灰,已經岌岌然要把他們燒成灰燼,屍骨無存。以一個反對者的姿態出現,而能被人發現,甚至進入選集中,贏得勇士的美名,不但非常幸運,而且,很有技巧。前舉蘇金傘〈頭髮〉一詩即為一例。岩上的〈那些手臂〉(註)亦為一例。雖然在內容意義上,該詩乃一首頌贊,然而,更引人注目之處,卻在其排比的形式。舖張揚厲的排比形式,容易模糊了內容主旨。歌頌那些「伸展成為樹/枯槁在空中」(註)的手臂,是否暗含對某些權力的控訴?詩裡不明顯。那麼,這首頌贊又著力於何處?歷史瘖啞,有血淚的往往無言詞,他們的悲哀不受認同,而軀殼轉瞬沒入蒿萊,與草木同朽。(註)
三、人體──作為一種冥思
所謂「以人體來冥思」,意謂詩人用較抽象、線性、一致、單一感覺的文字表達,呈現深刻反省中的「我」。這類作品往往帶動一種「快感式」(Pleasure)的閱讀(註),令讀者一讀為快,再讀回味。
描繪人體,以人體為冥思的對象,必得注意到「距離」引起的問題;距離太近,不免讓實際人生的聯想壓倒美感;距離太遠,又難以了解。例如默默的〈手指的流露〉(註),其中的「玫瑰的方向」、「波浪的方向」、「懸崖的方向」、「語言的方向」、「奇蹟的方向」、「夢的方向」、「歌聲的方向」、「媽媽的方向」、「城巿的方向」、「幻想的方向」、「時間的方向」、「你的方向」、「虛無的方向」,其節奏吸引讀者到純粹的意象世界中,於現實之外另闢一個世界。縱然這些「方向」令讀者莫明所以,卻未嘗沒有存在的理由─藉著文字排列及節奏,人生的距離推遠了,讀者可以暫時擺脫日常生活的限制,無黏無滯、聚精會神地欣賞詩人的手指運動(註)。
以人體為冥思的對象,常因文字營造出的距離而充滿晃動的疊影,在心理層面上,擺盪於認知/否認、洞見/不見之間。詩作中的人體呈現,可能因為詩人對文學的認知而有所隔閡,可能因為詩人的藝術人格而無法深入,也可能因為詩人的某些個人經驗,使得他只用特定方式描呈人體。鍾鼎文的〈人體素描〉(註)及商禽的〈五官素描〉(註)二詩,可為輔證。二者相較,鍾鼎文寫〈髮〉、〈乳〉、〈臂〉、〈臍〉、〈腳〉五詩,是從一個疏遠的、批評者的角度去對待這些題材,把它們當成客觀描繪的對象;商禽寫〈嘴〉、〈眉〉、〈鼻〉、〈眼〉、〈耳〉五詩,是在審查研究自己,把自己融入描繪的對象之內。〈人體素描〉充滿清簡的愉悅;〈五官素描〉面對冷漠的中年和勢必枯索的老年,充滿自我和現實的對抗、消長。例如〈眼〉:
一對相戀的魚
尾巴要在四十歲以後才出現
中間隔著一道鼻樑
有如我和我的家人
中間隔著一條海峽
這一輩子怕是無法相見的了
偶爾
也會混在一起
只是在夢中的他們的淚
此詩即為詩人個人經驗的烙痕。失鄉的痛苦、對原鄉的緬懷,也是這組詩作的根。詩人站在歷史的風口,任由一片逆耳而至的噪音高拔著分貝,既隔不斷漫天的囂囂,也不敢一刀除掉聽覺的苦惱,所以他說:
如果沒有雙手來幫忙
這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
然則請說吧
咒罵或贊揚
若是有人放屁
臭
是鼻子的事(註)
如果對詩人的失鄉經驗不了解,讀者與詩人就會缺乏對這組〈五官素描〉的默契,而有較大的詮釋分歧。相對之下,鍾鼎文的〈人體素描〉就沒有這方面的詮釋困難。〈五官素描〉中,個人經驗左右了詩的情趣,而詩人復為情趣所羈糜,當其憂喜,若不自勝。〈人體素描〉中,塵憂俗慮都洗濯淨盡,詩人無所營求也無所畏避,跳開所感受的情趣,站在一旁,冷靜地把情趣當作意象來觀賞玩索,想像中尚留一種餘波返照。例如〈臍〉:
從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口枯井,
它曾經為我們湧流過生命的活泉。
在它的斷流之日,我們的生命脫穎而出,
以第一聲啼哭,發表「獨立宣言」。
這歷史的遺跡,記下我們先天的恥辱,
顯示出我們的前身,原是吸血的寄生蟲。
每當我俯首默念,對著枯井懺悔,
啊,母親!對於你,我是永恆、永恆的罪人。
以枯井喻臍,兼具諷刺與諧趣。這個比喻放諸四海而皆準,無涉乎個人經驗,無關於時間切面,屬於一種小布爾喬亞階層的冷雋體察。詩人頭頂戴著一圈光環,在定居行走的空中樓閣裡冥思人體的意義;受到這種藝術人格的囿限,也使得作品終究只呈現安穩可人的風貌,難以透出生命的潮濕、黑暗或沃腴。而在商禽的〈五官素描〉中,詩人用整個肉體來叩問存在的價值,思索命定的規範(註),企求懷舊式的回歸,卻也難免限於自傷身世。
不論是沉湎於個人經驗或是侷限於藝術人格,以人體為冥思對象的詩作,都會面對一個基本質疑:人體在哪裡?詩人在冥思之前,是否有一個相對應的確切主體,來啟動其冥思?──詩作時或呈現的歧義,是否可以說是詩人在身體和語言對應中的語焉不祥?而如果「對號入座」,是否可以說是讀者的詮釋能力不夠呢?
或許可以用「轉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作品裡,身體和語言文字往往不是截然分裂或完全吻合,而是在文字符號投射的身體中游走、飄動,在字裡行間擴散。羅任玲的〈盲腸〉(註),鄉愁主題非常明確,「風起時/隱隱作痛」七字,作用於出末段「一截潰瘍的/鄉愁」,盲腸是轉喻的材料。唐捐的〈橘子和手〉則反覆辯證,探索橘子和手之間的互動:
手剝開橘子,才知道橘子
也有指頭。橘子剝開手
才知道終日緊握的手其實
只在包裝自己的溫柔
橘子的酸澀還沒通知舌頭
手的羞澀,又何必向橘子
透露。只是摸索摸索
向溫暖潮濕的處所
橘子的腦中藏有堅定的念頭
非喉頭所能消受,手的執著
又豈是果肉所能逃脫
用手的激情餵飽橘子
用橘子的沈默洗手
如果讀者堅持探問這首詩的主題,得到的答案可能是: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可是讀者可感受到此詩耐人尋味,可以察覺詩人好像在分析什麼,也可以感覺此詩的正文結構並不排斥分裂,可以接納(吸收)多種詮釋。此詩彷彿奧蘊極深,觸之似無物,究之終不盡。假設把它解讀為性愛詩,那麼詩人的步驟可能是:組織代表性欲的意象:橘子和手♂分析性愛的意義♂分析身體意象(手)所佔據的位置。「手」進入一連串意義的交換,而無法固定(或受因)於語言的牢房。正如詩人所言:
詩人用舊的詩浸泡著自己的身心,從而又分泌出新的詩,如此循環反覆,愈滲而愈濃,如同山茶花用淫淫的體味養活自己,因而愈來愈成其為山茶花。她從來沒想到用花果枝葉來反映環境,反而拼命排拒陽光和土壤對她的影響。她用自己的體味與世界區隔,以證明自己的超然。(註)
四、棄絕皮肉或脫胎換骨?──善待人體詩
《新詩三百首》中機關重重的人體素描,透露了這樣的訊息:資訊社會的新科技,不但沒有消弭身體的經驗,反而用更新、更激烈的方式對待身體,更強化身體的經驗。無論是冥思或論述,詩人逐漸開發自己的身體,析剔的角度也日趨冷酷。也許讀者不免打從心底同情這些詩人:如果美人的紅靨在他眼中不過是病兆,嬌弱的體態隱藏的無非衰竭,他們還能注意到容色之美嗎?還是所有身體的表徵都只是判斷意識型態憑藉?他們的得失何在?然而,豈不也因為像這樣越過了柔弱易感的階段,才成就詩作旁觀人生、嘻笑諷喻的冷雋?其得失又何在呢?而一個社會最可怕的是:大多數人蛻變成同質的身體,進而使少數的異質身體遭到排除。尊重,是進入人體的關鍵。
註釋
李孝定《續說文記‧卷十二》,頁二七○:「古文人體象形字,凡兩手相交者,均示有所操作。」中研究史語所,民國八十一年。《說文》之人體象形字,如「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耳,主聽者也,象形。」「目,人眼也,象形。」「自,鼻也,象鼻形。」「心,人心,在身之中,象形。」
宮體詩以濃豔的辭句、和諧的音律,描繪婦女的顏色、體態、服飾、居處、陳設。六朝梁武帝及庾肩吾、徐陵等,是宮體詩的能手。劉勰評為「繁采寡情,味之必厭」,鍾嶸也以為「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水滸傳》中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即為顯例。
此處乃就《新詩三百首》所收的作品而言。為舉證之便,不遑首首皆顧。
正文(text),或稱文本或本文,是「具有意義的東西」。如文字、語言、身體動作、現象、事件等等。有的時候,正文除了表面的主題外,好像還話中有話,這就表示正文底下還潛在著另一個正文,是謂:潛在正文(subtext)。
《管子‧入國》:「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謂之合獨。」合獨之風以鄭衛二國最為盛行。《詩經‧鄭風》的許多篇章,如〈溱洧〉、〈野有蔓草〉、〈風雨〉,都以輕鬆而歡快的筆觸,描寫男女的自由交往。
《新詩三百首》,張默、蕭蕭編,九歌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
例如林燿德、陳克華。其後還有顏艾琳等。如果不限文體,更有洪凌、李昂、紀大偉等。已然蔚為大觀。
Jouissance:狂喜、極樂、高潮。此代指耐心的、令人回味的、逐字逐句的閱讀方式。
本文尊重作者及作品的主體自主性,期待搜尋被不經意忽略的潛在文本。窺探,在本文中的意思,近於「掀開華麗的文字包裝」,並非不友善的偷窺,亦非羞辱。如有誤讀,尚祈海涵。
同註,頁五八二──五八四。
參見張小虹,〈越界認同──擬仿/學古/假仙的論述危機〉。收於氏著《慾望新地圖》,頁一五八──二○一,聯合文學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十月。
同前註。
陳克華,《欠砍頭詩》之代序〈猥褻之必要〉一文,提到:「生活原是一種態度,態度一失人生自此進退失據。文學不過白紙上的黑字,繪畫不過平面上的一點線面。一群人整天忙於擁頌一堆垃圾,再忙於指責另外一堆垃圾。人生至此,愈發突顯猥褻之必要。」(氏著《欠砍頭詩》,頁十六。九歌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而許悔之在評陳克華詩集《美麗深邃的亞細亞》時,以為「對陳克華而言,書寫些什麼已不是問題,踰越些什麼則在《美》集裡顯得進退維谷。相較於《欠砍頭詩》的情慾多樣,邪魔歪道,《美》集則溫良敦厚得許多,官能的顫慄(與暴力)美學不見了,《美》集的扮裝秀遂令人心有遺憾,好像表演者的手足被綑綁。」(許悔之,〈進退失據的扮裝秀〉,《聯合報》四七版,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九日)
同註,頁八三四──八三六。
此處詩行排行依《新詩三百首》。然原詩中「無能將你亟欲飛昇的頭顱強自深深眷戀的軀幹」,應為一行。
此乃《新詩三百首》附於〈我揀到一顆頭顱〉後,編者之評析。
又參,王浩威〈道德者陳克華〉:「更讓他(按:陳克華)如此迷戀這一切拆解分離器官的,毌寧是深藏在心裡的一股沙德式的激進理性主義,對於人類現實中所再現的一切事物,質疑或否定其表象,而拆除了它們表面的完整幻想。」(收於陳克華,《欠砍頭詩》,頁十一)在陳克華〈等到你也愛我的那時候〉一詩裡,詩人說:「一度,人們開始捨棄肉體/捨棄死,也捨棄生與飢渴/捨棄寂聊與滿足,眷慕與夢……/(中略):愛,的確/曾經存在/而且只能依附肉體」(陳克華,《美麗深邃的亞細亞》,頁九二,書林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六年)
奚爾芙曼(Kaja Silverman)在〈白皮膚,棕面具〉中,以勞倫斯(T‧E‧Lawrence)為例,認為勞倫斯的阿拉伯頭巾、飾環與絲袍的裝扮,是對阿拉伯建國運動的認同。其中也摻雜了受虐同性戀心理的糾葛。(Silverman, Kaja. “White Skin, Brown Masks: The Double Mimesis, or with Lawrence in Arabia.” Differences 1-3(Fall 1989):3-54)
生理性別(Sex),謂與生俱來的性別差異;如男女性徵。文化性別(Gender),謂後天社會、教會等制約加諸其上的性別差異;如陽剛、陰柔。
同註,頁一八二─一八六。
參見Anthony Synnott著,舒詩偉譯,〈墓穴‧神殿‧機器與自我─軀體的社會性建構〉。收於《島嶼邊緣》二卷二期(總號第六期),頁五─三二。
有時國家或政府基於「最大的善」立法,實際效果更是凶猛、不容懷疑。例如英國於一八六六年訂立〈傳染病法案〉,要求娼妓強制受檢;於一八七一年訂立〈種痘法案〉,把國家的控制直接注射到每個國民的血管內。正如傅珂所言:「四處都是警覺的凝視。」(參見傅珂〈十八世紀的健康政治〉,譯於《當代》七一期)
同註,頁五二二─五二四。
同前註,頁五二四。
在文學史裡,湮失了的天才就湮失了,不會成為例子。真正寂寞身後的,是那些不曾相識的名字。
Pleasure:快感。代指一種舒適的閱讀。
同註,頁一三三二。
同前註,編者評:「此詩乃作者於某夜借雙手的運動,展開一連串意象的探索。」
同註,頁三○三─三○六。
同註,頁四四一─四四四。
同前註,頁四四四,〈耳〉。
同前註,〈鼻〉:「沒有碑碣/哭穴的/墓/梁山伯和祝英台/就葬在這裡」。
同註,頁八七六。
鄭慧如
性別:女
籍貫:
出生地:
出生日期:
學經歷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台灣詩學季刊社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