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
所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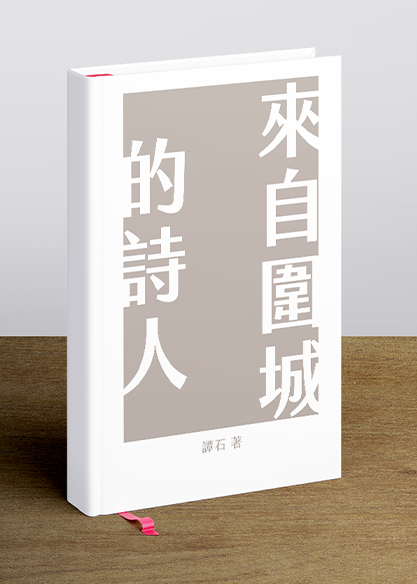
來自圍城的詩人
- 作者/ 譚石
- 發表/
- 發表日期/
──波蘭詩人茨畢格紐‧赫伯特
(Zbigniew Herbert)
從米洛虛談起
1980年,波蘭團結工聯的工人們聚在格旦斯克市的船塢,向世界宣稱:「自由、民主、尊嚴與自我決定生活的方式,是人類永不滅的希望之火!」;數個月以後,這一年的諾貝爾
文學獎宣佈頒給流亡卅年的波蘭詩人米洛虛(Czeslaw Milosz,1911──),因為他「以不妥協的敏銳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衝突世界中的暴露狀態」。
然而,波蘭的詩人,甚至任何其它文類的藝術創作者,誰人又不是處於「激烈衝突」的歷史中呢?
如果我們還記得蕭邦,這位鋼琴詩人在1980年波蘭起義失敗後,是如何將他民族的不幸,以悲憤的琴鍵傳給西歐人民;必然也應該知道,密茨凱維茨(Adam Mickiewicz,1793─1855)這位波蘭最偉大的詩人,一生為波蘭民族運動而遭迫害,甚至放逐西伯利亞的歷史。另兩位和他並稱三大浪漫主義詩人的:史洛瓦基(Juli-us Slowacki,1809-49)和克拉辛斯基(S. Krasinsky,1812-59),又何嘗不激動於那一不幸的時代,而寫下不朽的詩篇?
浪漫主義曾經是詩人參與社會的工具;到了十九世紀下半,寫實主義更是如此。女詩人郭諾甫尼加(Ma-ry Konopnicka)詩中對工人和農人的愛,以及對故鄉的愛;小說家顯克
維支和萊蒙脫更是代表。
米洛虛曾說:「革命詩,從藝術觀點看來,往往反而比關在象牙塔裡的藝術家的詩來得好,因為題材接近人類心中的渴望,使他的文字擺脫掉流行於當時的陳腔濫調上的束縛。」他也曾說:「革命詩只要一開始讚美……立刻會變得軟弱無力的。」只是,對波蘭的歷史而言,可以讚美的年代總是短促幾年就消失了。
對米洛虛而言,年輕時代參加左派活動而成立的〈第二代先鋒詩派〉,成為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激烈衝突」;二次大戰期間的反納粹運動是第二波;1951年,對共產主義的史達林主義的失望,從此所展開的卅年流亡生涯,是他漫長的第三次革命。
整整十五年只是寫給抽屜看
繼米洛虛之後,最受西方矚目的波蘭詩人要數茨畢格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了。1968年,英國企鵝版《現代歐洲詩人》系列推出他的選集以後,赫伯特的動向也就一
直受到注意,在德語、法語和英語的世界裡,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廣泛的翻譯和出版。然而他在美國的名聲,卻是這兩年才獲得廣泛的注意。這要歸功於詩集《來自圍城的報告》和文評
集《花園裡的野蠻人》,以及連續兩種版本《詩選集》的出版(一本是卡本特夫婦翻譯的,1977年出版;另一本是米洛虛和另一位合作的,去牛出版)。
赫伯特出生於1924年,比米洛虛小13歲。他的故鄉羅夫(Lvov)位於波蘭東側,是個典型的中歐城市。雖然二次大戰以後,這塊版圖遭蘇聯強行併吞,但赫伯特一直繼續以波蘭文來寫作。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也是一位經濟學教授;由於他的「父系祖先是十六世紀時離開英國的」,他們家族也就一直沿用著赫伯特這一個英國姓。
1941年,赫伯特才十七歲;當時德國納醉佔領了波蘭,他也匆忙結束高中課程,投入地下反抗軍的工作。直到戰爭結束後,他再到大學繼續修習他父親的職業:在克拉科修經濟,在Torun修法律。畢業以後,定居華沙,做著卡夫卡式的職業:銀行裡的辦事員、商店的職員、工廠裡的經理工作等等。
在投入地下軍的那一年,他也開始寫詩,然而在史達林時期結束以前,從不曾嘗試出版;他自己調侃這「整整十五年只是寫給抽屜看」。赫魯雪夫解凍那年,1956年,才有詩集出版:《一線之光》;次出出版《海爾梅斯、一隻狗和一顆星》;第三年又出版《客體的研究》。
從波蘭詩壇的主要流派來看,赫伯特算是〈第二代先鋒詩派〉一路的延續。一次大戰以前新浪漫主義的〈青年波蘭〉運動,在二○年代逐漸由〈絲卡嫚達〉詩派所取代,這是一個「要創新詩的語言,並從傳統的詩韻架構中求取完美的成就」的團體。在同一時期,另一個與它相抗衡的團體是〈第一代先鋒〉詩派,他們認為詩是「由暗喻組成的數學架構」,「詩人應該用最精簡的字,避開個人感情的直接發抒,從意象中創造出感情的等同體」。從1918到1939年,這兩個團體一直為著自己的主張而彼此攻訐。在兩次大戰之間,波蘭詩壇的另一支主流是普羅詩;他們的社會參與態度接促成了以米洛虛為首的〈第二代先鋒〉詩派。這些詩人在二次大戰前崛起,他們對上一輩的兩派詩人,〈絲卡嫚達〉和〈第一代先鋒〉,因為「彼此的爭執而陷入形式的死胡同」有所不滿,才有了更激進的主張:在內容上明顯地左傾,在形式上來得更簡單而有活力。
拒絕將真理棄置於任何口號之下
從西方詩壇的觀點來看,二次大戰以後西歐及英美等地最優秀的詩人大都從個人創作的經驗出發;然而,作為現代波蘭的詩人,是不可能避開這種屬於民族的集體創傷經驗。波蘭,歷經百年割據後終於在1918年恢復主權;不到二十年,卻又遭到德國納粹、二次大戰,以及史達林時期的摧殘。這樣的歷史,自然也就成為波蘭討人的背景;不論是四○年代崛起的米洛虛,或是六○年代解凍時期以後才出現的赫伯特,他們的詩裡總是透露出這一股政治態度。
經歷了地下軍反抗生活和史達林迫害時期的赫伯特,將自己十餘年來默默的創作比喻為「絕食時期」,認為這段時間給了他找到自己的態度而避開了外在的影響。他遲遲沒有出版詩集的原因,正如米洛虛所言,「在1956年以前,出版的代價等於宣稱了自己的品味;而他(赫伯特)並不希望做出這樣的付出」。
就做為一個「時代的見證」而言,我們可以稱他是政治詩人,雖然,在他的詩裡不容易找到明顯的政治主張。批評家A.Alvarez認為,赫伯特「是政治的,因為他持續而審慎地站在反對立場的美德……他的反對,並不陷入任何的口號:在納粹時期,他並不是共產黨人;在史達林時期,他也不以明顯的天主教徒或民族主義者自居。赫伯特的反對就像自己是個一人之黨,他拒絕將真理棄置於任何的口號。」然而,赫伯特也不認為自己是虛無主義的,他說:「虛無主義對文化的殘害是最大的」。
赫伯特的「政治」態度,也許可以從他對詩人角色的看法中略知一二吧。他一度表示:「在波蘭,我們認為詩人們是先知;詩人並不只是詩體的製造者,也不只是現實的模倣者。詩人應該表現出人民最深刻最廣泛的感受。……詩的語言不同於政治的語言。畢竟詩人比任何可以感受到的政治危機還要更耐命。詩人的視野超越廣闊的地域,超越光陰的延伸。他觀察著自己時代的問題,想要有所確定,但他只有在成為真理的黨人之際才可能是一位黨人。他引發了疑惑和不確定,對萬物處處質疑。」
喜歡面對歷史問題
赫伯特的詩裡,一種「不經心而颯颯低語」的聲音(米洛虛對他的形容),正可以形成這國家命運悲劇的共鳴。如果說聲音帶著希望,那又未免過於嚴肅了;如果說是虛無的,卻
又有著一絲的熱情。正如前面提到的,虛無的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在他眼中,都是一種特別的殘害;「在詩人的自我之外,展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雖然矇矓,卻是實在的。我們不該懷疑自己利用語言來掌握這個世界、對這世界下判斷的能力。」也許我們可以說,赫伯特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古典主義者。
這古典主義的作風,可以從他詩裡用聖經及希臘神話的明喻獲得最表層的證實。他喜歡面對歷史的問題,但他說這「並不是想要從其中學得教訓,而是要將自己的經驗拿來和其他人的經驗做比較」。而神話的運用,降低了時代的直接經驗所帶來的刺眼光芒,更可以從歷史事件的特殊侷限解放出來。
他成功地給合了幽默和諷刺,也是作品成功的原因之一。而他詩裡的想像力最突出的特色,應該是那一般帶有頑皮氣息的奇想了。這些特色,使得他詩的肌理都活潑起來了,成為
反抗思想上的集權控制的最有力武器。
當然,他的古典風格最根本的呈現,應該是文字的清晰和準確了。在《來自圍城的報告》裡,卡本特夫婦指出「他寧可壓低自己的聲音,而不願高揚;詩的節奏有時跡近於一種耳語,一種沉默的思考。」A.Alvarez則說「他以波蘭文寫成的原詩並不用標點符號,仍能呈現出明朗的風格;他的聲音雖然低沈,卻是清楚而準確。」這種清晰,正是他每一件作品的核心。
「我思先生」───本詩集的主角
他在解凍時期出版三本詩集以後,除了一本散文《花園裡的野蠻人》(1961)和劇本《戲劇》(1962),遲遲未有新的詩作結集。這時期間他曾一度定居國外(1965-71),也開始獲得國際間的矚目:得到幾個國際性的文學獎,在美國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教書,應邀出席重要的國際文學會議,以及最重要的,他的作品英譯選集在1968年由企鵝出版社印行。
1968年出版的詩集《題銘》反應平平,但74年的新詩集《我思先生》(Pan Cogito)卻引起批評界的普遍注意。Cogito這個字是拉丁文;所謂「Cogito,ergo sum」,也就是笛卡兒名言:「我思故我在」。
我思先生是貫穿這本詩集的主角,他是一位通俗的知識份子。他看報紙,困惑著一些問題:流行藝術、美國、異化、創作過程、一位老詩人,也喜歡回憶童年和家人。他的關心是很實際,生活十分平凡。他有許多弱點,包括缺乏在抽象思考的能力、對教條主義的排斥、十分人性的恐懼和焦慮、一些不當的感受和反應,以及自嘲的傾向;然而這些缺失娓娓道來,卻又成為我思先生的最大力量。
對赫伯特來說,戰爭和現實所帶來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對任何追求和諧、秩序和美的藝術都感到極大的懷疑。詩是服膺於真理的,而真理則忠於現實──不論是過去或是當前的現
實,不論是已發生或是將發生的。赫伯特從不稍減他追求的熱情。他筆下的我思先生也是如此;這角色的塑造並不是為了藝術的經營,而是一種見證:「……挺胸前去吧,穿過兩膝趴地的人群/越過臉龐朝地仆倒塵土的人群「你的獲救不是為了要活下去/你已不再有時間你必須發出證言」勇敢吧,當心靈欺騙著你時請勇敢吧/在一切的絡結,只有這才是重要的……」
他堅持著真理和美德的唯心主義態度,從某些角度來看,是一種執著的可愛;只是有時候,唯心的認同不免淪為偏執而釀成一股傷害力。最明顯的例子要前前年冬末,他發表在波蘭地下刊物《獨立文化》月刊上的一篇訪問稿了。用嚴厲的字眼鞭笞知名文人
在這一篇標題為〈每件事都照實招來〉,長達四十三頁的訪談裡,赫伯特用最嚴厲的字眼鞭苔了幾乎所有的波蘭知名文人。他說:「我希望不要直接提到任何人名,但是,歷史畢
竟不是由幽靈來寫成的。」於是他一一點名批判:安德烈朱斯基(Jerzy與鑽石》,他說那是奉命寫成;像華伊達(Andrej Wajda,波蘭最知名的電影導演,作品有「灰與鑽石」、「大理石人」、「鐵人」等),他說他在五○年代製作的第一部電影「一代」,有關一位年輕共產黨員參與反抗軍的故事,簡直令人「怒髮直豎」;他提到孔威奇(Tadeusz Konwicki)這位當前波蘭最傑出的小說家,從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時期直到像《小啟示錄》、《波蘭情結》這類有關波蘭人民生活之荒謬的作品,他以這樣的轉變指出一個作家是怎樣將自己的天賦轉為一種役用;甚至米洛虛這位流亡的諾貝爾詩人,也遭他指控「曾有極短的一段時間為了出版而寫作,為了政治目的來迎合靈魂的扭曲」。赫伯特自己表示:「我是很喜歡劊子手這一個角色的,但是,如果這是一場審判,我願列出這些罪名:(A)他們依著恐懼和壞信仰來行動;(B)他們是由虛榮心來驅動的;(C)他從基本的物質動機出發。」
波蘭的知識份子一直有著反抗的傳統,但是,反抗的行動往往很快就風消雲散了。1980年團結工聯運動,文人們紛紛投入行動;直到賈魯烈斯基將軍上台,宣佈了戒嚴法,這些知識份子依然暗中凝聚成「杯葛運動」的洶濤,拒絕自己的智識參與任何國家機器的運作。但是三兩年下來,堅持的人越來越少了。畢竟,生活的間題以及個人的名利慾望往往發散出不可抗拒的影響。在令人痛心的歷史事實裡,也難怪赫伯特會有這一番悲憤的談話。然而,赫伯特這些極具殺傷力的話,並未造成其他作家的憤怒反擊;畢竟,正如另一位波蘭作家所說的,「他(赫伯特)的作品是眾人早已肯定的,他的道德心更是眾人皆知的。」
他的詩是反抗野蠻人的武器
《來自圍城的報告》是1981年,汽蘭進入戒嚴法以後寫成的,也是他最新的詩集。當時,賈魯烈斯基將軍宣稱該國進入「戰爭狀態」;而這詩不但是這一段時期的描述,也是百年以來波蘭的故事:
我喜歡臨晚在這城的前哨漫遊
沿著我們不確定的笛由的前線
望著成群的士兵在自己的燈光下
傾聽野蠻人尖銳的咚咚鼓聲
的確真不敢相信這城依然繼續保
衛著自己
包圍已經許久了而敵人必然能夠
成功
殲滅我們所有人的慾望促成了他
們的團結
哥德人韃靼人瑞典人這些變形帝
國的軍隊
誰能數清他們呢
他們旗幟的顏色變換著一如地平
線上的森林
從春天巧鳥的黃轉為綠轉為紅再
轉成冬天的黑
這些作品令人聯想到他早年的散文集《花園裡的野蠻人》,在這些散文裡,他談起歐洲不同時代的野蠻人入侵,對那些文明花園,像法國、義大利、古希臘所造成的影響;再從這些主題延伸向一些被消滅的文明,以及它們所遭遇的殘暴破壞。
也許,在赫伯特心中,他的詩就是反抗野蠻人的武器吧。他怒視著俄羅斯、德國、奧地利這些凌辱波蘭歷史的「野蠻人」,用低沈的聲音來完成他的時代見證。他不和野蠻人合作的態度,一直堅持著,即使波蘭政府允諾出版他的作品不做任何的修改,但他依然將出版工作委託巴黎的一位出版商。他說:「這些日子以來,波蘭政府根本不把地下文化發生的事放在眼裡。他們只想將文化恢復正常化:每一個人都繼續地寫一如往日……」,而他作品的出版,其實只是促成了波蘭政府正常化的企圖。
從五○年代以來,赫伯特逐漸成為波蘭文學的反抗象徵;他的道德態度和詩風更影響了下一輩的年輕詩人。他的作品呈現出昔日源自地中海的世界標準與當代東歐經驗之間的差異,而這也是他最迷人的影響力之一。至於他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從這些年的報導看來,相信將會越來越受重視了。
參考書目:
1.A.Alvarez”Noble Poet”The NewYork Review,July 18,1986.
2.M.T.Kaufman”When Bedbugs Atethe Fleas-Politics and Writing in Poland”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86.
3.E.Hoffman “Remembering Poland”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Feb.16,1986.
4.B.& J.Carpenter”The Recent Poetryof Zbigniew Herbert”World Litera-ture Today,Spring, 1977.
5.S.Miller “The Poetry of ZbigniewHerbert”,1977.
6.J.Pilling “An Introduction to 50Modern European Poets”Pan Books,1982.
7.Czeslaw Milosz “Post-War Polish Poetry” UC press,1983.
8.William Riggan “The 1984 Jarorsand Their Candidates for 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WLT,1984-i.
文章出處:
現代詩復刊10期
譚石
性別:男
籍貫:
出生地:
出生日期:一九六0年
學經歷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曾為台大醫院、和信醫院及慈濟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並為《島嶼邊緣》文化雜誌總編輯;目前為專任心理治療師,台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及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