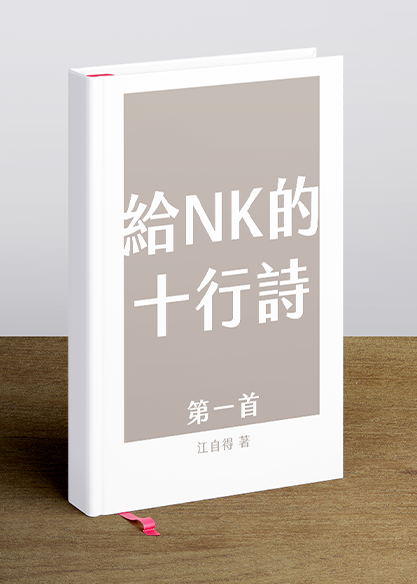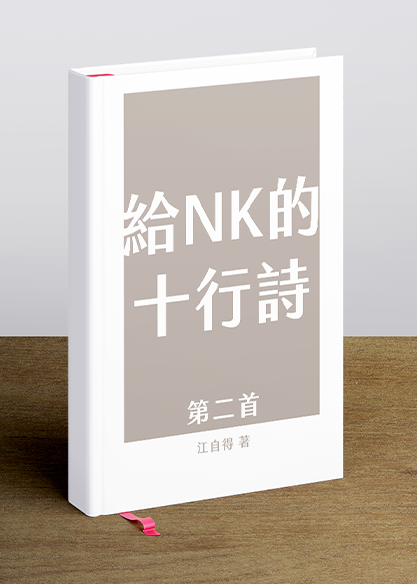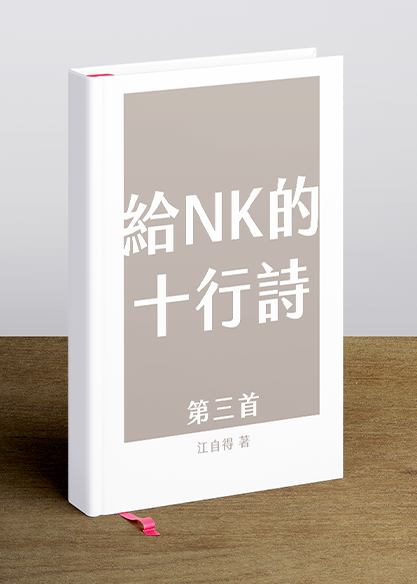所有作品


出了門你就在黑暗中
夜深人靜,我試著用低一點的聲音說話, 但它們總是高出我的意外,張著黑色的 巨大的翅膀,撞擊著我關了一半的窗子, 告訴你,天黑不是好藉口,家裡可能飛 走的孩子也不是,出了門你就在黑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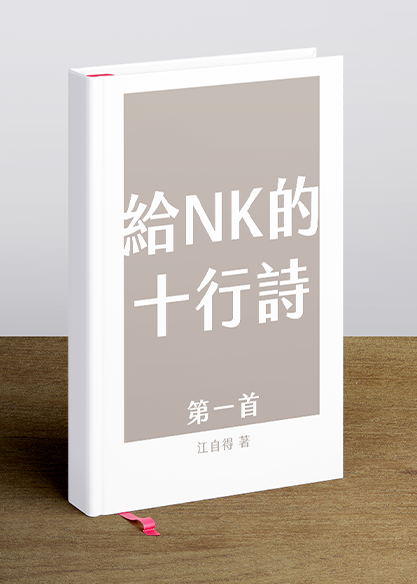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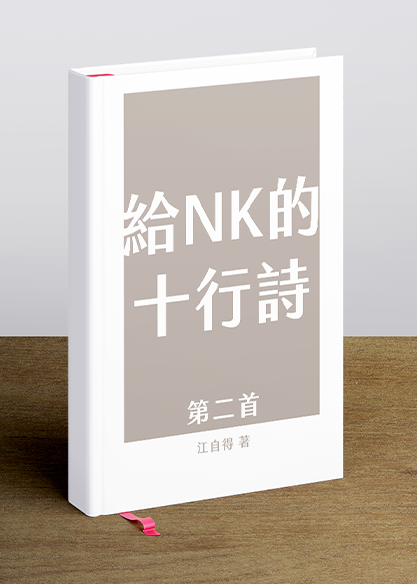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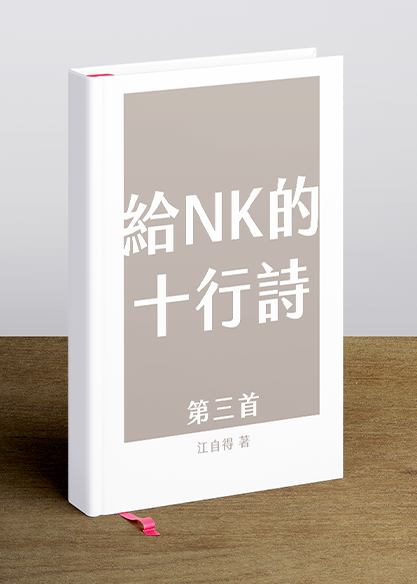


夜深人靜,我試著用低一點的聲音說話, 但它們總是高出我的意外,張著黑色的 巨大的翅膀,撞擊著我關了一半的窗子, 告訴你,天黑不是好藉口,家裡可能飛 走的孩子也不是,出了門你就在黑暗中。